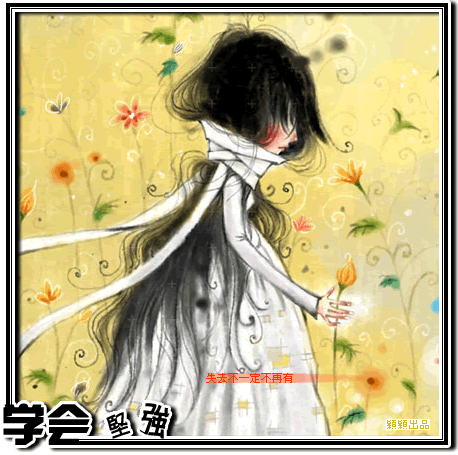
坚 强
李玉燕
晚风轻拂着衣裳,夕阳依山落下,我的心也如同针沉入海底。哎!这次考得太差了,漫步在无人的石板路上,我好迷茫,找不到方向。一股寒风袭来,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弄得我那伤口好痛。
那是一条真实的伤口。
在我六岁那年,我患了急性阑尾炎。由于医生的误诊,使我的病情在悄悄恶化,当发现时,不得不动手术。才六岁的我,平时连轻轻摔倒都要大哭一场,哪儿经得起手术的折磨,想到医生用光亮亮的刀在我的身上划一道口时我就胆颤。这时是我的父母,用他们温暖的手紧握我那怕得打哆嗦的小手,用他们和蔼的眼神看着我,告诉我:孩子,坚强些。望着他们的眼睛,我顿时有了无穷的勇气,我的两手不再颤抖,呼吸不再急促。我平静的被推进手术室。当进入手术室的瞬间,我给了他们一个灿烂的笑容。手术从准备到结束,我都没有掉一滴泪水,真的,我的眼睛根本没有湿润过,我现在还吃惊我当时哪来的勇气。
就在以为我手术成功不久就可以出院的时候,全家人被另一张医疗报告单吓倒了——我又患了阑尾炎导致的肠粘连,这意味着还有一次手术。一家人默默地坐在那儿,母亲坐不住了,起身走到外面,我知道她在哭泣,她是在担心我。她在担心我那幼小而虚弱的身体怎能再次承受一刀,她在心疼,心疼她可爱的女儿又要面临伤痛。如果可以,我知道母亲宁愿那刀子在自己身上开几个口子……
手术还是要进行的,不管父母有多么不想,我有多么不愿,总不能让我无法进食而死去吧。第二天,医生来到病房,说是手术准备。具体的话我无也记不清了,总之说是要在我腹部的两侧凿一个小洞,把管探进去清理一下。我不知道那一个小时我是怎么过的,父亲再一次用他那温暖的手握紧我,而我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床单。
“快好了,快好了”,我隐约听见医生在安慰我。之后,也许疼晕了,当我醒来,父亲握着我另一只手睡着了。我转头看了看父亲的手,已经被我抓破,而且血肉模糊。我哭了,住院以后第一次哭了。我轻轻地拿起父亲的手,可不争气的泪珠正好落在父亲手上。他醒了,看见我正看着他那双惨不忍睹的手,笑着打趣的说:“小家伙的力还蛮大的哟。”然后走了出去。至今,父亲手上还有一块伤疤。那一块凹凸不平,疙疙瘩瘩的伤痕,就是当时我给父亲留下的。
手术如期进行,由于父母的鼓励,我仍然很平静地进了手术室。躺在手术台上,迷迷糊糊看见一个医生正在用比平时的针管大好几倍的针给我推葡萄糖,接着就有十多个护士围着我,白压压的一片。他们在我的全身找血管,头上、手上、腿上甚至脚背也不放过,也许是由于这几天一直在输血,所以血管不好找。因此这些针一次又一次扎进我的皮肤,却没有一根进入我的血管。全身上下的疼痛伴着恐惧,不知道下一会儿又会哪儿疼,这次我真的想哭。但我没有,因为我不要父母失望,不要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那么不勇敢。我忍耐着,咬紧牙忍耐着无比的疼痛……
动完手术后是不能饮食的,也不能喝水。看见邻床的病人虽然出同样忍受疼痛,但总还能吃上香甜可口的饭菜,痛饮一杯平时我毫不在意的开水,我真的是嫉妒得要死。慢慢的我可以喝水了,但都少得可怜,我只能抿很少一点,连邻床阿姨的小孩都同情我。倒满了一杯水,递给我说:“小姐姐,你快喝吧!”想起我那时真是可怜。可父母也没好受,为了不让我难受,他们从不在我眼前吃饭,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吃的饭。
受了这么多苦。总该可以出院了,可是X光却发现我体内还有一个不小的液泡,于是还要进行第三次手术。我后来听说,第三次手术差一点我就被阎王招去了,据说我离死亡只有半步。在第三次手术进行时,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死,我要让父母再一次为我的坚强而骄傲,要知道在一个月里,经历三次手术我都没因伤病痛而哭过,我的确够坚强。我没有死,因为死亡无法带走一个拥有父母无限的爱的可爱的女孩!
第三次手术后,母亲告诉我,我身上的血乎全都换掉,也就是说,我身上流着无数个献血者的血。我突然来了动力,提出要跑几步给母亲看。母亲答应让她扶着我慢慢走几步。因为我在床上躺得太久了,可没想到我在伤口还没有拆线的情况下挣脱了母亲,快乐地跑着,跳着。我要让母亲不要再为我担心,我要让她知道我好了,我健康了,他们可以放心了。但其实我的脑子全是晕的,有几次差点都要摔倒。
我是从死亡边缘被拉回的人,是父母的关怀以及鼓励让我有了求生的欲望。那么就算是为了他们,为了母亲不再流泪,为了让父亲的手上的伤口不再疼痛,我也应该坚强。这小小的考试失败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我会这样沉沦下去?
独自走在石板路上,随意地四处张望。突然有一星红色映入我的眼帘,她很小,却在寒风中开得很艳,很艳!
评语: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知道这个故事很真实的人,无不对这个故事的经历者油然而生怜意与敬意,特别是年长的为人父为人母者。
作者是凭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去写出这篇文章的,因为毅力,也因为亲身经历,于是她从一种书面表达的木讷中冲了出来,表现出一种从容与自信。
她很小,却在寒风中开得很艳,很艳。